文/周纬萌
抵抗、支撑、平衡、依赖……在马刺画廊“无量之物”的现场,乌雷(Ulay,Frank Uwe Laysiepen)受中国长城建筑启发而作的雕塑《门,98》与他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1980年合作的行为艺术《静止能量》的影像在空间上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这件大型铝制雕塑由左右两个弧形构成外轮廓,中间牵引出对抗的张力。
这恰恰和《静止能量》中二人身体与弓箭构建出的空间与情感关系如出一辙:两个极度自我的灵魂在爱、信任和对抗的过程中用生命的重量拉开弓箭,在危机与依赖的反复纠缠中,探索人与人间的共生极限。


这是乌雷在亚洲的首次个展,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情人·长城》自然而然被赋予重要篇幅,其中不可避免地谈到他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与关系。在展览开篇的走廊两侧分置从嘉峪关出发的乌雷和从山海关出发的阿布拉莫维奇的旅程录像,历时90天,他们最终在长城之上的相遇,但相遇的拥抱却成为了二人分离的见证,《情人·长城》也是二人合作的最后一个项目。
然而,这件代表了结果的影像仅仅是长城项目在“无量之物”展览中的起点,更多追随乌雷视角的宝丽来照片、日记、诗歌与手稿追溯了他在跋涉过程中遇到的人、事、景,以及对爱与情感、边界与生命的喟叹与感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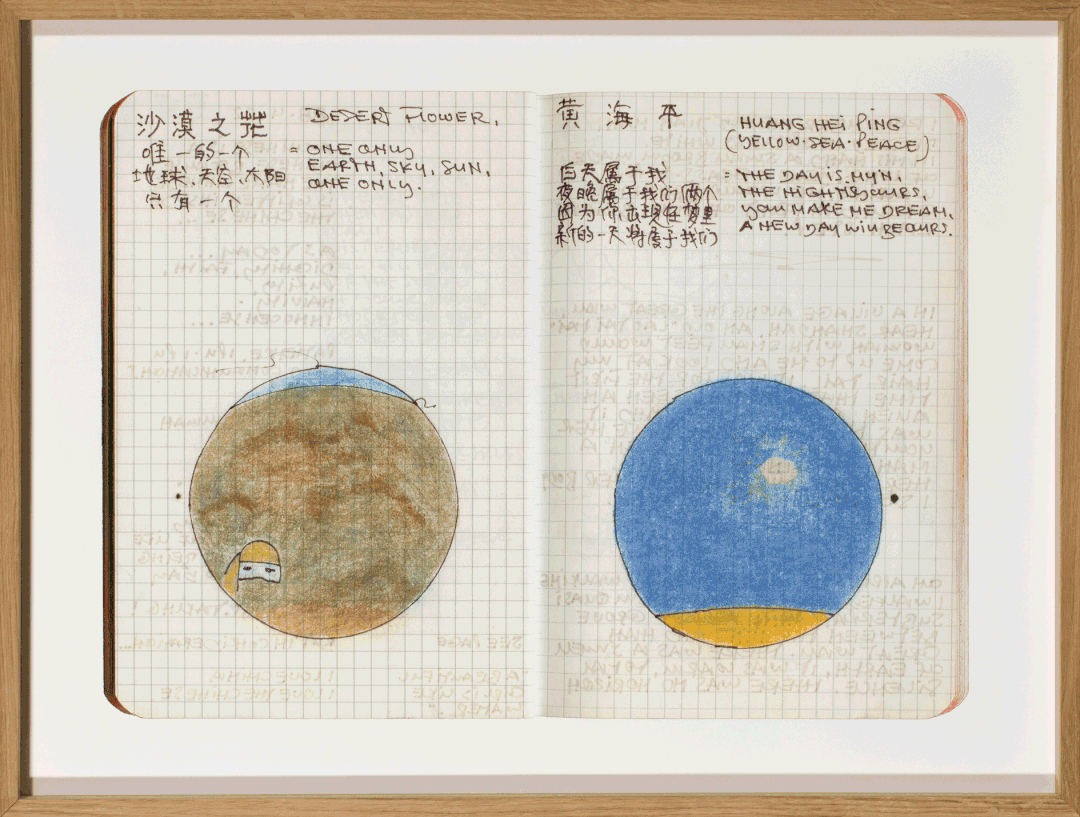
穿透自我:宝丽来与“他/她”
乌雷在中国身份证明中有一个汉译名“悟来”,它在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义了乌雷的身份属性,又如一个崭新的灵魂挤入了“乌雷”的身体中。
对“身份”议题的关注一直延续在乌雷的创作生涯中,早期的宝丽来摄影真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乌雷选择在镜头中探索、塑造与暴露这种女性意识的具体形象,让这个来源于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挣脱束缚、大胆分享“乌雷”这具身体。
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乌雷在社会边缘群体(异装、跨性别者等)中找到了这种复合身份的共鸣,他在镜头的快速捕捉与迅速成像、拼贴与重构图像中坦然地展示了身体中两种灵魂的博弈与共存,对感性与理性、性别与身体在个体与公共的认知层面下做出了先锋性的探索。



很快,乌雷就不满足于宝丽来摄影在讨论身份问题时仅能触及的表层捕捉,他开始设想如果要挖掘自我的基因编码与身份本质,就必须想方设法深入身体的表皮之下。从这时起,乌雷对自己的身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剖析手段,以纹身、切割、穿刺、缝合、植皮等行为将身体一点点拆解、曝光在镜头的审视之中,他面对镜头记录与表演,进而开始了一系列“行为摄影”的创作。这或许是乌雷创作中极为疯狂和感性的一段历程,他迫切想要走近一个“真实”的自己,挖掘“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穿透“白盒子”:从镜头到行为
乌雷的摄影开始越来越富有行动性,他持续探索着表演行为与摄影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博弈,渐渐的,“表演”开始突破摄影的媒介框定而走向真正发生在公共空间的“行为艺术”。
1976年,在Fototot项目中,乌雷将空间改造成了一间“暗室”,观众入场后,在特殊灯光的作用下,悬挂在墙上的“艺术作品”中的图像在短短15秒内瞬间消失,只留下一片黑暗的底色,在场者热烈地讨论着艺术作品中图像的去向与艺术家的创作用意。


随后,乌雷开始在替代性空间中开始进行真正的“行为艺术”创作,而创作方式的突破也伴随着乌雷从讨论身份在自我认知层面的探索转向对身份在公共空间与社会语境中复杂境遇的触及。在第一次读出“行为”(performance)一词时,乌雷想到了另一个词,“穿孔”(perforation),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乌雷在回忆这个最初的解读时说:“我希望将有生命的艺术注射进白盒子画廊与博物馆中”【1】,在当时的系列艺术行为中,乌雷都展现出了对白盒子空间和传统博物馆展览的挑衅与质疑。
在《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中,他将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的《可怜的诗人》从博物馆偷走,并带着这幅能颇能唤起自己德国身份属性的作品来到了当地一户土耳其家庭的家中,并以此替换了墙上的装饰画。乌雷称希望借此行为,将移民、种族壁垒与歧视等现实议题引入博物馆、艺术机构的讨论之中【2】。

穿透关系:合作与共生的极限
在1976年至1988年间,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乌雷对身份与关系议题的探讨在更多维度中的发生。在二人相识之前,他们各自的艺术创作都有着极强的个人风格与力量,他们在思考:两个完全独立自治的个体、两种迥异而尖锐的力量如何能够共同作用于一件作品的创作?
在随后二人合作的《空间中的关系》、《光明/黑暗》、《时间中的关系》、《呼气/吸气》、《AAA-AAA》、《静止能量》、《无量之物》等行为艺术中,他们深刻介入了亲密关系之中的共生与依存、个性与趋同、碰撞与裂痕等讨论,也以极为观念地表演抽离出了人与人间的关系中那些隐于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的痛苦、创伤与恐惧。
最初在替代性空间进行的系列行为表演使二人的创作独立于艺术市场的主导与制约,但同时,他们以自我身体为媒介带来的行为合作爆发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能量,如一把极为尖锐地匕首刺透了彼时尚且“保守”的艺术语境。然而,这种身体与身体、关系与关系间巨大而紧密的探索强度的背后,是二人在生理和精神层面必须保持的高度依赖与共生,对于两个同样独立而尖锐的灵魂而言,这种高强度的共生关系或许在最初就预示着二人间的复杂情感终将被燃烧殆尽。



穿透生命:回归与再启程
乌雷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个人创作在媒介层面显示出了对摄影的回归。通过对摄影本质的溯源,他注意到人类的视觉感知经验和负片残象间的关系,对媒介的反思进一步和他关注的“身份”议题相结合,乌雷开始审视当代社会中边缘化的个体以及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民族主义、历史废墟、城市表皮及其背后的符号隐喻。
乌雷在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的一个防空洞内,这使他成长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与家庭环境之中,或许自出生起,对德国历史与民族性的记忆就一直扎根在乌雷的心中,在艺术表达的探索历程中,这种记忆终将在某一阶段被自然而然转化为艺术创作母题,并予以极度个性而经验化的表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中,乌雷坚持探索在摄影与行为表演之间的维度,更大尺幅的宝丽来摄影开始出现,自拍系列也在延伸着。
2011年,一部影片计划在乌雷心中酝酿,然而在同年秋天,他被诊断出淋巴癌。几经放弃的影片计划在导演达姆扬·科佐勒(Damjan Kozole)的坚持下开始于化疗后的乌雷的病房之中,这个最终命名为《癌症计划》的影片项目最终让一直以身体为媒介揭示复杂多元关系的乌雷回归到了自己的身体。
和早期那些极端地、迫切地想要进入代表自我的身体的阶段不同,与癌症的相处带给了乌雷一种剖析人类躯体、人与人、人与外部环境之关系的全新视角,在这场被视作告别影片中,乌雷拜访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与曾经工作的地方。
在这场再度由自己演绎的行走计划与身体实验中,乌雷似乎实现了与自己身体和身份的和解,但却仍在用镜头的语言延续着对围绕世界的种种关系的讨论,譬如边界与生死。



“也许我把自己看作始终不愿被社会接受的人,而我无论如何也从未与社会为友”,乌雷在“无量之物”展览现场的纪录片中如此说道。这位先锋摄影、行为艺术家在五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中始终锐利地试图穿透、剖开与撞击着什么,他从对自我的认知出发,以刺破自己的皮肤表层、深入皮囊之下的血肉为途径,随后将自我的对话与低语以行为表演的方式演绎出来。
当他的行为从镜头中挣脱出来时,又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驱动着他去对抗艺术世界中的白盒子空间和其中既有的展览内容与观看模式:他想要刺破这堵代表着传统、精英与经典的“白墙”,挑衅艺术市场主导下的艺术创作与艺术家身份,带来一些更为鲜活而赤裸的生活与现场。
这种穿透式的艺术思考从个体身体与经验出发,最终弥散至多元的文化特质与广泛的民族身份,更牵连出人与人间从身体到精神层面复杂而流动着的情感与关系。




乌雷在2020年最终离开了这个他一直在试图更了解一些的世界,“理解乌雷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正如阿布拉莫维奇所言,由毕生创作堆积而成的厚度仍无法诠释“乌雷”,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抵抗与突破世界和经验赋予他的身份与定义。
文|周纬萌
图|除特殊标注外致谢乌雷基金会与马刺画廊
注释:
参考资料:
关于展览:

乌雷:无量之物
策展人:来梦馨、哈娜·奥斯坦·奥日博尔特
2022年9月4日至10月30日
Gallery I & II|SPURS Gallery,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二号院 798 艺术区 D-06
——来源|中央美院艺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