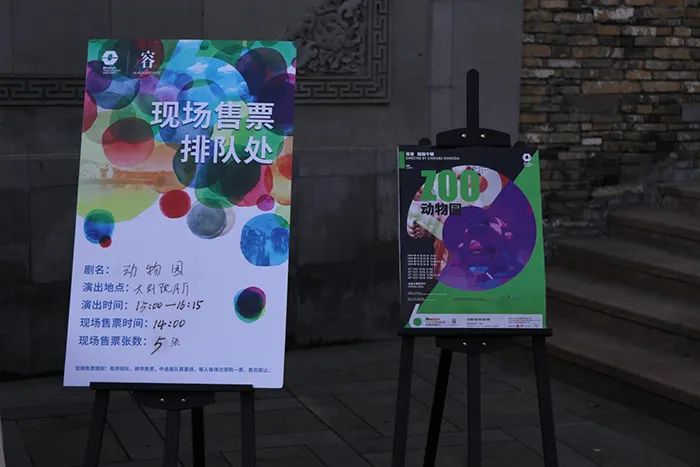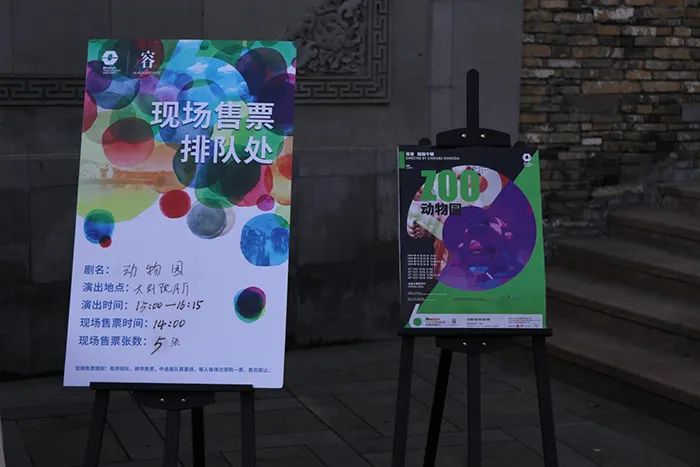访谈:艺术节庆热潮中小城镇如何激发活力
时间:2022-07-05 19:15:59
编辑:晓钟
文/肖剑、刘鹏飞
中国近些年来,兴起了一股艺术节庆的热潮,以艺术节庆为旅游助力,为游客和观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综合体验,给行业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但众多小城镇节庆渐渐陷入同质化和后继乏力的困境,在全国范围内有品牌影响力的地方艺术节庆寥寥,如何有效激活小城镇和乡村艺术节庆的活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肖剑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美学与传播、公共艺术介入、媒介与文化分析等,近年来她多次实地探访过平遥、乌镇、连州、方峪村等城乡的专业艺术节庆,对地方艺术节庆活力的关键因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近日,艺术中国记者对肖剑做了独家专访。艺术中国:乌镇戏剧节和平遥电影节不太一样,乌镇戏剧节更多的是地方主导者陈向宏全盘规划,艺术家策划实施;平遥电影节最初是以电影导演贾樟柯个人来推动形成的地方节庆品牌,你感觉每个节庆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肖剑:我考察地方节庆的方法是民族志法,这是一种沉浸式的方法和视角。我先说平遥电影节和乌镇戏剧节的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形成了一个自在的空间。平遥和乌镇有自己建筑的特点,平遥有平遥电影宫,乌镇有乌镇大剧院和多个分众剧场。以后者为例,当乌镇戏剧节开幕的时候,组织者会把乌镇的很多地点都挪用过去从而形成一个空间体系。在平遥电影节,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爱好者们告诉我,他们认为平遥是不一样的。比如一线城市举办的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它们都没有这样一个空间体系。我觉得这是一线城市的局限,不太可能找到这样的场地,即使有,维护成本也很高。在北京或是上海电影节期间,大城市观众虽然看电影的时间也很集中,但也只是像平时一样看电影。而在平遥电影节,观众需要花一段时间住在平遥才能真正体验平遥电影节。乌镇戏剧节就更为明显,很多爱好者看完戏,在景区里游玩的时候都有可能见到戏剧工作者,我记得2018年我们就在景区里偶遇了金士杰老师。这种情况无论对于爱好者还是我来说,都会有遁世感、乌托邦感和专业感,观众在那里不仅有良好的感知体验,在戏剧、电影本身的专业性上也会有提升。平遥电影节和乌镇戏剧节还有一个共同点,既借鉴了国外的节庆方式,也继承了它们的先锋精神。比如阿维尼翁戏剧节、戛纳电影节这两个节庆都是为了反对当时法国整个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巴黎等中心城市,它们提出把节庆放在巴黎以外边缘的地方,充分体现了艺术的先锋和反叛精神。平遥电影节和乌镇戏剧节传承到了这一点。除了电影和戏剧内容很先锋之外,它们采取的“远离大城市,到更小的城市里建设”这种艺术节庆本身就是很先锋的事情。 目前,文艺工作者在乡村和城镇做节庆活动是很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比如国家提倡文艺工作者要到乡村、小城和县域地区去实践,但我觉得当下这些文艺工作者也不完全是为了迎合国家文化战略,而是一种恰好。大城市里的文化很繁荣很丰富,但还是配合着大城市居民的高压力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城市居民在欣赏艺术活动的时候,往往不是一种放松休憩的状态。但当他们来到更小的城市和乡镇参加艺术活动,反而能在新的、近乎隔离的空间中体验到艺术带来的自由和美。艺术中国:贾樟柯主导的平遥电影节一个重要环节是非西方电影展映,联想到他众多电影中表达的地方感,你认为他推介的非西方电影是否可以理解为全球地方感的影视呈现?肖剑:贾樟柯是国际知名导演,他的电影方式和他的地方感结合的特别紧密。贾导的很多著名的作品都是在山西拍摄的,所以他的电影节之梦一开始就放在了山西,希望能够从山西出发,走向全球。我觉得“全球化”是个后殖民的概念。当我们理解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时候,这种全球视角还是带有强烈的西方视角。其实我们身处于这个时代,即使足不出户也依然生活在全球的联结中,沉浸在全球化的地方体验中。然而,贾樟柯有一个视角的转变,提出非西方电影,与全球现在对知识生产系统中强调“全球南方”的诉求相呼应,更是在全球板块中有自己的文化声音。在贾樟柯的组织理念中,世界版图中的东亚、东南亚系列、大都市背景下的小城经验,都构成了他对于非西方的一个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抗衡美国文化霸权,还暗含着对权威城市的一个挑战。艺术中国:某种角度看,平遥电影节和乌镇戏剧节仍然属于精英文化,吸引的是全国电影或戏剧界的大咖和爱好者,当地居民对此是否有足够的接纳? 肖剑:我们现在经常就艺术介入城镇或是乡村提出问题:能不能真正渗透到居民日常的生活中去,能不能和本地结合,能不能真正发生影响?这与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问题密切关联,即艺术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过程还是受到文化关系等的影响,通常我们认为自律他律会共同作用。我在乌镇戏剧节期间采访了戏剧节的组织者黄磊并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在乘坐出租车时问司机知不知道乌镇戏剧节,司机表示对戏剧节并不关心,那么您是否认为这表示着戏剧节无法融入本地人生活。黄磊则回答,为什么要每一个人都融入和认同?这种融入与否的问题其实也体现着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矛盾。另外,本地居民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论本地居民时,视野都比较窄,但事实上本地居民的层次丰富,范围也比较广。比如与平遥电影节相对的“本地居民”这个概念就有很多层次:山西人、平遥古城外的居民、平遥古城内的居民等。古城里都是做旅游观光生意的人,他们有观影的热情,有些人也会去看明星走红毯、看电影,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平遥电影节看成经济来源。而对于平遥整个地方居民甚至说扩大到山西,可能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深刻。比如平遥电影节中有许多当地人自己拍摄的影像。贾樟柯现在是山西电影学院的院长,自然也会带动很多山西本地人前去学习。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形态比较稳固,但教育却能让孩子们受益,从中受到影响。艺术中国:艺术节庆对本地居民产生具体影响还有哪些有趣的例子?肖剑:当时我去山东的方裕村参加方裕村戏剧节的时候,感觉那里非常有趣。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古老村子,那里召集村民看戏的方式还是用大喇叭喊,但就在这里我确凿地体验到“当地居民受到了艺术影响”。以前我觉得受到艺术影响就是他们会非常喜爱这个艺术,或者跟我们去探讨艺术的意义,但是方裕村村民欣赏艺术贴近艺术的方式就是他们认为亲近熟络。方峪村戏剧节主要是一些外国剧团在演出,他们有自己排演的方式。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剧团在古戏台的表演。我当时采访日本剧团的人,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的户外环境中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从现代语境来看,他们本应该在更为密闭的室内空间里演出,但在方裕村的户外演出让他们有了另类的体验。戏台后面还有行驶的拖拉机,还有其他影响表演的情况,但当地居民很喜欢。有一个老奶奶搬来小板凳坐到舞台很近的地方,非常认真的观看表演。方裕村村民对于戏剧的亲近感能从他们的姿态和行为看出来,村民在观看戏剧的时候都不是正襟危坐的一个状态,而是边嗑瓜子边闲聊的状态,村民对这种戏剧氛围是很亲近很喜欢的,所以有这样放松的姿态,这其实也和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氛围很相似。莎士比亚时期人们看戏剧的方式也都是非常放松和市井的。我当时也去了村里本地剧团的现场,那里主要表演京剧或地方戏,现场的观剧方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方式也非常相似,闲聊着,很放松。我当时就感觉这才是观众与艺术融为一体。如果我们问当地某一个居民对戏剧的感受、意义和价值,他可能谈不出什么。但他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像他看京剧或者地方戏一样。所以到底本地居民和艺术产生了什么连接呢,我觉得不仅要对本地居民的范围进行扩大,思考连接的形式也要扩大。不管是艺术本身对它产生了吸引力,还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对他有吸引力,只要能唤醒他的熟悉感和连接感,我觉得就是成功的。艺术中国:连州摄影节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广东的连州小城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摄影节也没有太多摄影文化的氛围,但这样一个学术化的摄影节能在连州持续了十几年,形成了一个国际品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肖剑:我去了三次连州摄影节,我能感觉到当地政府支持力度非常大。连州摄影节的开幕展和其他地方节庆不一样,开幕时的观众和展览容纳的人数非常多。它和平遥电影节也不一样,平遥开幕式中主要吸引人的是走红毯环节,准入的门槛也比较高,也并不是很多人能进去观看。但连州摄影节把整个仪式放在大广场里面,能够吸引到非常多的人。那么即使这些人本身对摄影没有太大兴趣,但他们会因为这个仪式认为它很重要很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连州摄影节能举办这么多次,还是政府支持的力度比较大,无论是拔高还是强调,当地政府让这个节庆在某段时间内成为了连州的重心。艺术中国: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地方营造或艺术乡建,地方的节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但现在有很多艺术节的例子中,节庆中的艺术也许很好,但在当地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你觉得上述较为成功的例子是在于主办者能和当地政府和居民产生更好的参与互动吗?肖剑:“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可能是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体系,可能是让本地居民感动,也可能是构建了城市品牌。地方节庆有政府主导,也有艺术家主导。平遥电影节作为后者是很突出的。但我们再仔细观察平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节庆小城,本身有很多节庆。我当时采访政府官员,他们提到平遥电影节、平遥摄影节和平遥雕塑节是平遥精英式的、专业的节庆,但平遥的春节反而是地方节庆里面参与人数最多,最具吸引力的。他提到地方节庆和专业性的节庆吸引到的观众不一样,影响的层面也不一样,可以吸引专业观众,也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事实上,很多地方节庆失败的原因是大量复制,没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平遥、连州还有乌镇这些地方都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同时,艺术的社会功能虽然越来越重要,但艺术乡建和节庆生产并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它们只占到乡村振兴里面很小的部分,我们在考虑地方营造或乡村振兴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考虑艺术功能,应该在多元的网络关系中考量。艺术中国:地方节庆里面的因素比较复杂,可能是诸多因素因缘巧合凑在一起恰好导致了某些地方节庆的成功。肖剑:是啊,如果这么容易成功,那么艺术还是艺术吗?那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艺术本来就具有先锋性,有些地方可以容纳这种先锋性,有的地方并不能,我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之韩国舞台剧《Madame Freedom》艺术中国:你考察的地方节庆的艺术形式主要是戏剧、电影和摄影,而当代艺术节能在小城镇或乡村连续举办十年以上的情况,目前在中国是很难看到的,这是不是说明地方上的居民对更为当代艺术化、更为先锋性的节庆还缺乏认同?肖剑:我在英国爱丁堡的时候,当地有两种不同的艺术节,一个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它是一种精英式的、大多基于室内的节庆模式。当时爱丁堡一些人为了反对这种艺术风格,就创建了爱丁堡艺穗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实行了另一种模式,艺术节中的很多活动在户外展开,艺术形式很多也都是行为艺术,这种方式可能比装置和雕塑更能被观众理解。我也分别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节采访过相关的负责人。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nding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总监乔纳森爵士的策划性非常强,他会亲自寻找艺术家,精心策划整个艺术节,呈现艺术节的专业性,所以艺术节和当地观众产生互动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并不是很重要,他认为艺术专业性能让更多的人领略艺术的极致。这个总监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声誉和头衔,呈现了非常精英化的状态。他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与城市发生关系的见解,都源于他精英化的理解方式。而爱丁堡艺穗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强调打破精英模式,希望艺术发生在任何人的周围。它认同的方式就是没有什么规则,谁想要去表演,哪怕是刚刚入行一两年的艺术家都可以去艺穗节里表演。所以如果以爱丁堡为例的话,地方节庆需要哪些观众来参与,就会决定用什么样的模式。现在很多艺术生产的方式就是建设博物馆、艺术馆或书店。我觉得这个方式有好有坏,这样的举措等于把一些原本很公共的空间变成半公共的空间,书店和艺术馆可以算公共空间,但是因为它有了边界,尤其在疫情的时候还需要打卡,这样的空间就变得不那么“公共”了,所以我觉得激活节庆的活力还不在于艺术的媒介形式,节庆的互动性和流动性的组织方式可能更为关键。要真正想要和当地人发生互动的话,可能就要换一种让人和人之间产生紧密联系的方式。肖剑:乌镇戏剧节有一个“狂欢”环节,也会邀请青年艺术家在这个环节参加户外演出。当然他们的形式还是戏剧的形式,不像艺穗节那样多种多样。(受访人:肖剑 采访人:刘鹏飞 图片来源:肖剑)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介与文化分析博士,兼任国际文化研究学会(ACS)理事,浙江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青云文社研究所学术主持,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起“艺术与媒介”(AMF) 国际论坛,原英国《Nottingham Evening Post》记者,英国“New Art Exchange” 美术馆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校外指导老师,积极参与当代艺术与公共讨论,与艺术机构、艺术家合作研究与创作。出版英文专著《Punk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朋克研究), 中文专著《影像-城市-历史: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
——来源:艺术中国